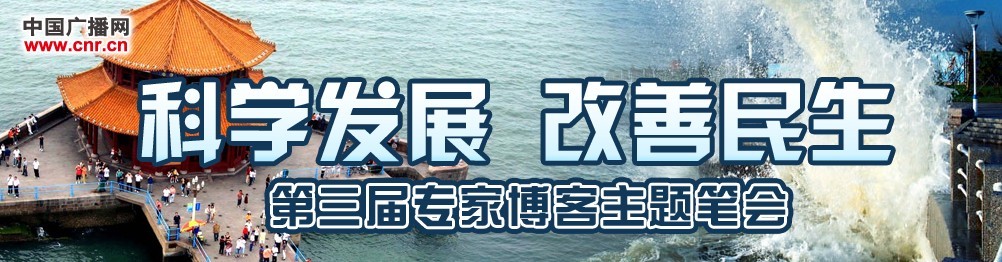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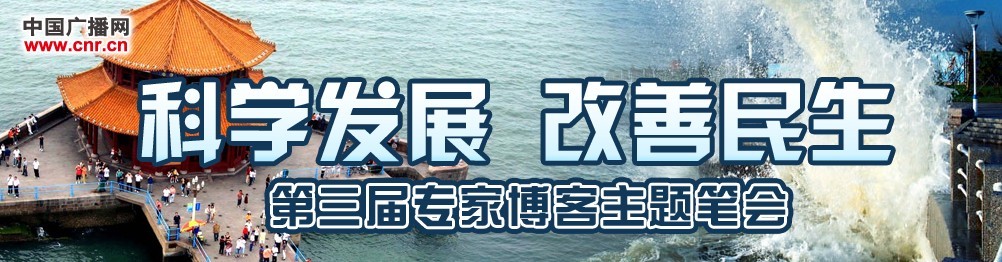
来青岛一般都去海边,青岛在人们的印象中也是蓝色的,特别是在旅游者的印象中。
但对于青岛本土人来说,海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如内陆文化来得深刻。比如与海联系最紧密的青岛港,就远远的在城市的西边,整个区域都被围起来,门口都有警察把守。我跟许多青岛人聊天,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港口城市。
而青岛的海滩也与城市有很明显的界限,这条界限是一条漂亮宽敞的滨海大道,道路朝海的一边建有许多二三层的小建筑,相互之间没有缝隙,如果你想下沙滩去散步,就必须沿路去找那些建筑之间的缺口,然后下很高的台阶才能到达。
有时候我打车从这条路经过,那些建筑把海挡得根本看不见,我还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内陆城市里旅行。
更多的本地人住在那些地势更高、更内陆一些的老房子里,也就是青岛的中部,这些房子多半都经过数代人的传递,街巷曲折复杂,街道两边都是高大斑驳的石壁,有些铁门早已锈腐,黄色的墙壁和棕色的窗框记录外来文明入侵的痕迹。海滩在夏天人头攒动,冬天寂寞寒冷,对于居住在这里的青岛人来说好像并没有太大关联,这里拥有的,只是宁静而缓慢的生活。
在小巷里搜索历史的痕迹
范伦是标准的青岛美女,个子高高的,好身材,面庞清秀、平和。我们在青岛海洋大学附近的一条安静的小路上碰到她,那时候她和她的朋友正从一个弯儿里拐出来,还没见人我就听到她爽朗的笑声。我上去和她搭腔,聊起这片老城区,她看着我和同伴气喘吁吁、满头大汗的样子忍不住又笑了,说一看你们就不是本地人,肯定是走不惯青岛起起伏伏的街道,没这个脚力。我说要是有辆自行车在这边转起来就方便了。“啊?”她很惊讶地看着我说,“你看青岛街上有几个人骑自行车?那可比走着还累呢!”
青岛的街道的确很怪,东部那些新区还可以,马路宽,直,很平坦,一到中部老城所有的街巷都变得陡起来。有的道路过于陡峭,干脆被青岛人换成了台阶,或是一种叫“菠萝油子”的路面。范伦告诉我“菠萝油子”路其实就是用很小的砖面铺成的马路,因为砖面上有很多纹路,离远看就像菠萝皮一般,遂得其名,“油子”是说长年累月,被磨得锃亮。
我一时间对“菠萝油子”感了兴趣,在老城里到处找、打听,但几乎所有地方都是柏油路。有老人告诉我,德国人在青岛的时候这种路有很多,但这几年因为政府改造城市,这种路面不方便行车,就都换了柏油,现在保存的听说也就三四条。在天主教堂附近有两条,有一条极宽,起伏着伸展下去,远处则是沉浸在暮霭中的夕阳和无数尖顶,真有些欧洲古城的味道。
观象山下面的观象一路和二路是两条安静而有趣的小巷。
小巷里到处都是灰色和黄色,一边是巨石垒起的很高的墙壁,朝海的一面则是矮墙,后面都是日本人在青岛留下的建筑。后来我走了老城的许多街道,发现所有街道两边都有这样的墙壁,房屋都是“包裹”在这些墙壁后面的。小鱼山那边街道的墙壁更好看,不仅被漆成很打眼的黄色,而且墙上有四方的花纹,墙顶有很好看的铁护栏,遇到下坡的时候,墙壁会像台阶一样一级一级地降低。据当地人说,这种墙叫“挡风墙”,挡的是海风。
如果在青岛的老城区里多逛上几天,你很容易在街上碰到一些可能是数年或数十年前才能看到的玩意儿,比如一辆二八加重的自行车,或是一辆生了锈的老式三轮摩托。它们一般都静静地靠在墙边上,落满灰尘。有一次我走累了,跑到一个小店里想买水喝,发现门口放了一个大啤酒罐,老板是个40多岁的男人,他迎出来说这是专卖“散啤”的,“散啤”——在我记忆中,8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没有这样的业务了。“这生意在北京肯定做不起来,但在青岛十几年了都不错,一般小店里都有,”老板骄傲地说,“青岛人爱喝啤酒,简直是每时每刻都喝,跟喝水一样。”接着哈哈哈地露齿大笑。可我还在那里傻呆呆地觉得奇怪,“我也想喝,可没东西盛怎么喝啊?”老板闻听从墙上摘下一个塑料口袋,竟然用这口袋接了满满一袋啤酒,用弹簧秤称了递给我,“青岛人都是这么买的。”我一点都没想到!接着他又递给我一个吸管。“用尖的那头扎。”我用吸管把塑料口袋扎破,用力嘬了一口,一股清凉的啤酒一下子涌进嘴里,瞬间倦意皆无。
责编:臧鸿熠 来源:四川在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