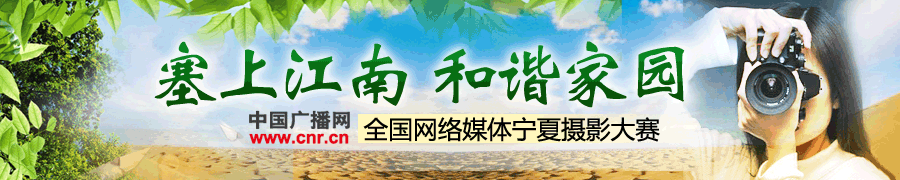回族的形成和发展
中广网 2010-06-25
[打印本页] [字号 大 中 小] [关闭]
住在“番坊”内的商人,虽然世界各国都有,但人数最多的还是波斯和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。唐朝为尊重其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,并使其自己管理自己,曾任命番坊中最有德望的人为“都番长”,以处理其内部事务,还允其于聚居区内建礼拜寺以从事宗教活动。宋朱彧《萍州可谈》云:“广州番坊,海外诸国人所居住。置番长一人,管勾番坊公事,专切招邀番商。”9世纪中期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《游记》中说:“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。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,教堂一所”。“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(广州),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,依回教风俗,治理回民。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,朗读先圣戒训……一切皆能依《可兰经》(《古兰经》)、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”。这些寄籍“番商”,有的后来长期寄居于中国,娶妻生子,并接受汉族文化影响,改用汉族姓名,习儒书,以适应其生活的环境。有的仕宦于当朝,如848年(唐宣宗大中二年)以进士显名的李彦升,据说就是原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商人。五代时又有颇具诗名的李珣兄妹,祖先也是移居于四川的波斯商人。878年(唐乾符五年)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时,据载住在广州的伊斯兰教徒、基督教徒、犹太人等,前后被杀者有12万人。数字或不免夸大,但其中穆斯林商人占多数似可肯定。
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,政治、经济虽远不如唐代兴盛,但因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政策,经海路到广州、泉州、明州(宁波)、杭州等地贸易定居的波斯、阿拉伯等国商人,比唐代还多。他们从事象牙、犀角、珍珠、香料等的运输和贩卖,大都获利甚丰,成为各地的巨富。《泉州府志》载当时:“胡贾航海踵至,其富者资巨万,列居城南。”如巨商蒲寿庚家族,据说就是先居广州后移居泉州的。《广东通志》亦云:“海舶贾蕃,以珠犀为之货,丛委于地,号称富庶。”为了攫取巨大利润,有的人甚至千方百计请求到内地州郡经营。部分穆斯林手工业者、宗教职业者等也相继前来定居,从而使前来寄居的穆斯林不断增加,并逐渐出现“土生番客”及“五世番客”诸名目。
除商人和宗教职业者外,还有部分来自阿拉伯的士兵。据记载,755年(唐天宝十四年),安禄山反唐,唐政府派兵镇压,并请大食出兵援助。757年(唐至德二年),大食阿拔斯朝哈里发遣兵参加平叛。平定后,这支部队并未被遣回,而是滞居于沙苑(今陕西省大荔县南洛、渭二河间),后遂发展为沙苑回民的一部分。《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》一书说,清代西北地区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,祖先就是唐时受命参加平叛而落籍于陕西的。
以上所述诸人,在整个回回民族来源中所占比例并不大,其最主要来源还是13世纪初年以后,自中亚等地陆续迁入的各地回回人。
中亚回回人东渐,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中亚引起的结果。从现有记载看,蒙古军在前后数次远征中,至少曾掳掠了十数万人解送回中国。例如1221年春,蒙古军在攻破撒麻耳干(撒马尔罕)时,成吉思汗便将其工匠3万人分给诸子和族人送回;又从被俘的青壮年中,选择同样数量的人签发为军。不久,在夺取花刺子模都城玉龙杰赤(今中亚土库曼境内乌尔根奇)时,又将其妇女和孩子俘为奴隶,将10万左右工匠遣送中国北方。1223年窝阔台率军进攻哥疾宁,当城他被攻克后,蒙古军队除对该城进行洗劫外,又将“工匠”、“手艺人”解送回国。此后,拔都、绰儿马罕、旭烈兀等西征,又陆续有部分人被发遣东迁,加上部分自愿投降蒙古军的人,其数字显然不在少数。
成吉思汗国以前,居住于蒙古地区的回回商人就不少,例如札八儿火者、马哈木·牙刺瓦赤、阿里火者、哈散哈只等,就是其中的著名者。1217年奉成吉思汗命令前往花刺子模贸易商团450人就全是回回人。随着蒙古贵族势力的扩大,中亚各地穆斯林商人自愿东徙的也很多。他们或从事从中亚至蒙古地区的长途贩运,或充当蒙古统治阶级的“斡脱户”(官商户)为各级王公贵族放高利贷。这些人在东迁的回回人中也占有一定比例。
以上诸项回回,是尔后形成回回民族的重要基础。
诚然,汉、维吾尔、蒙古等各族成员,也是构成回回民族的重要成分之一,但无论如何,他们都不是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。
责编:陈钟 来源:新华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