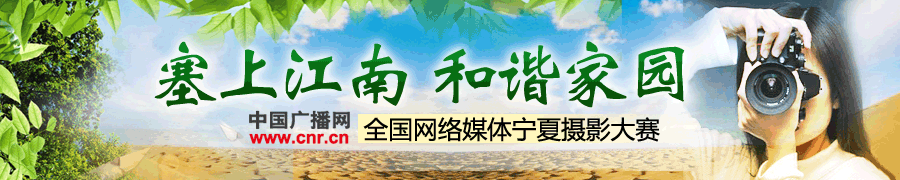回族的形成和发展
中广网 2010-06-25
[打印本页] [字号 大 中 小] [关闭]
散居在各地的回回人,因信仰伊斯兰教关系,他们往往自成村落,聚居于礼拜寺附近,形成大量的回回村、回回营、回回屯。在城市中,则逐步出现回回人居住的街区。从而使人口分布形成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格局。各地回回人正是依靠着这样的格局维持着彼此间的联系。他们实际上仍然有“共同地域”。有些人否认回回人拥有“共同地域”,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由于回回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,又都共同信仰伊斯兰教,随着岁月的推移,往来更加密切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往也不断得到加强,并逐步产生共同的利害关系,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。所谓“天下回回是一家”,“回回见面三分亲”,回回“行责居送,千里不持粮”的说法,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反映。回回人对阿拉伯文化、波斯文化的兴趣,与此也有一定联系。
回回人初到中国,他们大都讲阿拉伯语或波斯语,基本上还保持着原来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。名字大都仍由带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译,如马哈木·牙老瓦赤、扎马刺丁、赛典赤赡思丁、马合木、阿里、伊思马因等等,都是很好的例证。但由于居住分散,大多数人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,久而久之,其后裔便逐渐学会汉语,并“舍弓马而诵诗书”,接受汉族儒家思想,提倡讲求儒家经典,尊崇忠孝仁爱等伦理观念,喜爱汉族的诗、词、赋、曲。例如著名学者赡思,自幼“从儒先生问学”,“日记古经传至千言”。及至20岁时,又就学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门下,后竟成为一位“博极群籍”的儒家硕学。又如萨都刺、薛超吾(马九皋)、伯笃鲁丁、丁野夫、丁鹤年等人,不仅精通汉族语言,且皆以诗名世。买闾和哲马鲁丁,还以力资兼善学,分别成为嘉兴和镇江路儒学教授。哈刺鲁人伯颜,亦以精通儒家经典而成为当时名士。由于汉文化的熏陶,有的还改用汉姓名,按汉族习惯为自己取“字”;有的在使用原来名字的同时,又取一个汉姓。如哈只哈心子凯霖,改汉姓“荀”,取字“和叔”;薛超吾,改汉姓“马”,取字“昂夫”、号九皋;伯笃鲁丁,改汉姓“鲁”,取字“至道”;萨都刺,字“天赐”;买闾,字“兼善”;赡思,字“得之”;哲马鲁丁,字“师鲁”;别里沙,字“彦诚”。类似的例子很多,不胜枚举。在他们看来,“居中夏声名文物之区”,“衣被乎书诗,服行乎礼义,而氏名犹从乎旧”,实于理不合,应随时变通自己的习俗,才能更好地与广大汉族人民相处。诚如一位仕元官员凯霖所说,“居是土也,服食是土也,是土之人与居也,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,居是而有见也,亦惟择其是而从焉”。正说明了回回人在与广大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,已在逐步中国化。王礼《麟原集》也说:“西域之仕于中朝,学于南夏,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。岁久家成,日暮途远,尚何屑屑首丘乎?”
明朝初年,明太祖朱元璋因蒙古统治阶级过去曾歧视压迫汉族人民,欲反其道而行,下令“禁胡服、胡语、胡姓名”。还规定不许自相嫁娶。诏令颁行后,立刻在全国各地掀起一场“更易姓氏”的风潮,持续二年,许多蒙古、色目仕人都纷纷要求更改姓名。后明太祖发觉这样做对监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行动不利,又下令禁“更易姓氏”,并表示,“蒙古诸色人等,皆吾赤子,果有材能,一体擢用”。但更易姓氏之风非但不能遏止,反而有所扩大和发展。朱元璋宣布“禁胡服、胡语、胡姓名”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民族压迫政策,但由于在客观上与广大回回人对汉文化的追求相一致,因而后虽一再下令禁“更易姓氏”,却出现有禁而不能止的怪现象。正由于这样,尔后汉语也逐渐变成回回民族的共同语言。明末王岱舆等以汉文阐述伊斯兰教教理,实际上就是为了适应广大回回群众使用汉语文的客观要求。
责编:陈钟 来源:新华网